2025-03-02 編輯部
約翰·韋恩(John Wayne,1907年5月26日-1979年6月11日),這位好萊塢的傳奇硬漢,曾以銀幕上的牛仔與軍人形象,成為美國「見義勇為」與「維護正義」精神的象徵。他的角色總是堅毅果敢,對抗邪惡,捍衛弱者,體現了美國文化中那份獨立、勇敢與道德的理想。然而,當我們審視當今美國的政治舞台,尤其是唐納德·川普總統的外交與內政作為時,不禁要問:那個約翰·韋恩精神哪去了?
銀幕英雄與現實領袖的落差
約翰·韋恩的電影中,正義從不妥協。他在《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中跋涉千里拯救親人,在《真實的勇氣》(True Grit, 1969)中不顧年邁為女孩討回公道。他的形象與美國的「黃金時代」——一個強調自由、民主與全球領導力的時代——緊密相連。這種精神在冷戰時期尤為顯著,美國以道德高地自居,團結盟友,對抗蘇聯這樣的威權勢力。
反觀川普,他的第二次總統任期(2025年起)雖以「恢復黃金時代」為號召,卻與韋恩的精神漸行漸遠。他自詡談判高手,確實在第一任期促成了《美墨加協議》、亞伯拉罕協議等成果,展現了某種實用主義的成功。然而,他對外政策的基調卻是交易而非原則。他與習近平、金正恩、普京稱兄道弟,誇讚他們的強勢,卻對民主盟友冷嘲熱諷,甚至在2025年2月28日公開「臭罵」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約翰·韋恩的牛仔會與獨裁者握手言和嗎?恐怕不會——他的馬鞍只為正義而備。
對內肅敵,對外妥協的矛盾
更令人困惑的是,川普在國內外的態度截然不同。在美國,他是意識形態的旗手,將民主黨與黨內異己塑造成「深層國家」的叛徒,誓言清算政敵。他的言辭火藥味十足,一項未經證實的消息說,川普2025年上任後即推動對前眾議長佩洛西等人調查,彷彿國內政敵是比俄羅斯或中國更可怕的威脅。這種對內的零和博弈,讓美國的分裂雪上加霜。
然而,轉向國際舞台,意識形態卻從他的字典中消失。他淡化獨裁者的人權劣跡,稱普京「沒對美國做什麼壞事」,與金正恩的握手更成了「友情的見證」。這種內外反差令人費解:為何國內政敵比外部敵人更可惡?為何對內非要肅清不可,對外卻能與威權領導人談笑風生?約翰·韋恩的正義從不因對手是內外而有所偏倚,他對邪惡的態度一視同仁。而川普的正義,似乎只在選舉地圖上才有顏色。
美國精神的轉向?
川普的支持者或許會辯稱,這是「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摒棄意識形態的束縛,才能在混亂的世界中贏得利益。他的俄烏停火談判、美加墨關稅妥協,確實展現了交易型外交的短期成效。然而,這種策略犧牲了什麼?美國的盟友關係搖搖欲墜,北約的團結受到質疑,民主陣營的道德號召力正在消退。當川普要求烏克蘭交出資源作為支持的「報酬」,當他對歐洲施壓卻對俄羅斯示好,我們看到的是韋恩式的英雄主義,還是商場上的算計?
約翰·韋恩的美國,是站出來對抗不公的領袖,是弱者的保護者,是自由的燈塔。而川普的美國,似乎更像一個精明的生意人,計算著每一筆交易的得失。他的外交不以民主為旗幟,他的內政卻以分化為武器。這與韋恩精神的核心——正義與勇氣——背道而馳。
精神遺失的代價
川普的策略或許能在短期內帶來談判桌上的勝利,但長遠看,美國的「約翰·韋恩精神」正在消逝。那個團結盟友、捍衛原則、以道德引領世界的美國,是否已被一個只問利潤、不問是非的版本所取代?當國內政敵被視為頭號大患,當獨裁者成為談判桌上的「兄弟」,我們不禁要問:美國的靈魂還剩下多少?
或許,約翰·韋恩的時代已成過去。但他的精神——那份不妥協的正義與勇敢——仍是美國值得追尋的理想。川普的「黃金時代」若只停留在交易的表面,而非精神的復興,那麼美國失去的,可能遠比他談判桌上贏得的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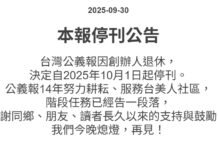
congress-218x150.jpg)
-218x150.jpg)
30日在維吉尼亞州對數百名美國高階軍官前發表演說。(美聯社)-218x150.jpg)

Trump-218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