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30【六都春秋】
.png)
文/余杰
孫文和蔣介石畢竟不是蘇聯從一開始起培養的代理人,對蘇俄的忠誠度並非百分之百。孫文生前沒有背叛蘇俄,但其接班人蔣介石在得到江浙財團和英美的支持後就與蘇聯分道揚鑣。因此,蘇俄決定專門開設學校,培養忠於蘇俄甚於忠於其祖國的中國革命者。蘇俄開辦的東方大學、中山大學的畢業生,逐漸取代留日和留英美的青年,佔據國共兩黨之要津。
「以俄為師」特務頭子 在「大清洗」中歷練的共產核心
二十世紀中國「以俄為師」的兩個典型人物是康生和蔣經國,他們分別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內讓人聞風喪膽的特務頭子。他們在蘇聯的生活有四年重合期,那時康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是蘇聯扶持的中共領袖王明的副手;而作為「人民公敵」蔣介石兒子的蔣經國,則是被王明和康生隨意羞辱的人質。
康生出身於山東大地主家庭,曾就讀於傳教士創辦的青島禮賢中學——這段學生生涯對他的世界觀毫無影響,這表明西方教會在中國創辦的教育系統已失去傳播基督教觀念秩序的能力,因為它們的創辦人自己都不具備此種觀念秩序,其學生自然被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左翼進步主義所俘獲。

後來,康生來到上海,參與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一九三三年,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崩潰,康生奉命赴莫斯科受訓,在此後的四年中完成其政治教育並成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他頻繁而密切地同蘇聯秘密警察來往,度過了史達林「大清洗」時期最黑暗和恐怖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個共產黨國家裡秘密警察的價值。[1]
康生不是「大清洗」的旁觀者。自封精通馬列的王明、康生主導了「大清洗」中的「小清洗」——即針對在蘇聯的中共黨員群體的肅反,他們全面照搬蘇聯的辦法:對看不順眼的同事做出開除黨籍、勞動改造、流放、坐牢甚至處死的處罰——蔣經國就是受害者之一。在異國他鄉,他們為了迎合蘇聯政治的需要而上演了同室操戈的一幕。
恐懼才是獨裁的培養皿 億萬人的未來早被玩轉手中
康生從國民黨在上海對共產黨的圍剿戰中倖存下來,對恐怖的環境並不陌生。但他發現,蘇聯是一個真正的警察國家,與蔣介石的統治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康生並不只是掌握了逮捕、拷問和處決對手的簡單技術細節——他更發現了如何使用恐懼來作為壓制政治異端的手段,如何將最荒謬無稽的虛假招供轉變成強有力的工具,以及如何使那些可能會告發他或試圖取代他的敵人緘口不言的方法。
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後,發現毛澤東已是黨內冉冉升起的新星。與毛相比,只會引用馬列教條的王明頓時黯然失色。王明在與毛爭權失利後,康生迅速投靠毛澤東,他運用關鍵的手段是「美人計」,他向毛澤東引薦美艷的文藝女青年江青——當年,江青的母親是康生家的洗衣傭人。工於心計的江青讓毛著迷並成為毛的新夫人。這種政治結盟讓康生受益匪淺:一九三八年八月安全機構的大改組中,康生被任命為延安兩個最有權力和最兇險的組織的負責人:軍事委員會情報部,它協調所有軍事情報工作;社會保衛部,它處理內部的安全工作和對反共敵人的情報工作。
在毛澤東確立黨內最高領袖地位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充當其首席打手。作家蕭軍是整風運動的親歷者,他在日記中記載: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此後「搶救運動」進入一個高潮。[2]
這場整風運動是由毛澤東策劃、康生實施,是兩人第一次完美的合作,也是文革之預演。延安整風不僅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如歷史學者高華所說,延安政府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蔣經國下放勞動 蘇聯經驗成奪權關鍵
康生在延安推廣的方法和公安工作形式,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後的時代。他那種將間諜活動的問題融入日常政治生活的傾向經常復發。他將一種痛苦的、血淋淋的、永久的遺產贈給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蘇關係在一九六〇年代破裂了,康生這名「留蘇派」卻在其他「留蘇派」被清洗之際,升任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權力之大,幾乎僅次於毛。
康生在蘇聯只生活了四年,蔣經國在蘇聯則整整生活了十二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孫文遺囑希望國民黨與蘇聯「合力共作」,莫斯科中山大學應運而生。國民黨要員子女中有五十人赴蘇留學,與蔣經國一起抵達莫斯科的還有馮玉祥女兒馮弗能(兩人一度戀愛並同居)、于右任的女兒于秀芝等,鄧小平差不多同時從巴黎來到莫斯科。蔣經國先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蘇聯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名叫《革命必先革心》的文章,鼓吹「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這一篇蔣經國在留蘇期間最早的文字記錄,被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將這位年僅十五歲的作者拔擢為《紅牆》的編輯。

蔣經國在蘇聯的十二年,過著亦工亦農亦軍的生活,比養尊處優的康生艱困得多。他曾被下放到工廠做苦工,到農村種地,「農民是毫無智識的,不講道理的。我初到的時候,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有一家肯借床鋪給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個教堂的車房裡」最艱難的日子是基洛夫刺殺案之後的肅反高潮,蔣經國被內務部監視起來,每天都有兩個人跟蹤他,除了工廠就是宿舍,不能見任何人,更不能和戀人蔣方良相見。他處於半軟禁狀態,隨時可能被捕。蘇聯經驗使他有超越於一般中國政客的智慧、手段和韌性,最終擊潰黨內群雄,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父親遺留的最高權位。
蔣經國回國之後聲稱他完成了從「媚蘇式共產主義」到「反蘇式共產主義」的思想轉變,但實際上蘇聯模式伴隨其一生——聯共(布)黨內各種思潮以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史達林模式,包括殘酷鎮壓敵對勢力、肅反擴大化、加強政治工作、控制意識形態、計畫經濟、統制經濟、集體農業等,給他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抗戰期間,蔣經國在贛南推行《建設贛南三年計畫》,正是模仿蘇聯五年經濟建設計畫的產物。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打虎」,推行的也是統制經濟。他仇視資本主義,號稱打倒「豪門資本」,包括與蔣家有姻親關係的孔、宋家族。所以,孔、宋家族長期不信任他,稱之為「俄羅斯兒子」——更何況他帶回了俄裔妻子。蔣經國敵視富人,聲稱「他們的財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之上」,這明顯是受托洛茨基民粹主義思想影響——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曾被當做托派受到批鬥。
蔣經國和大多數獨裁者一樣,缺乏文化素養、摧殘人權、不尊重生命。台灣學者吳乃德指出:
除了來台灣之前或許讀過古書王陽明之外,蔣經國似乎沒有閱讀當代較嚴肅的作品,無論是人文還是社會科學的著作。他的一些言論和著作顯示,他最喜歡、最精讀的書是他父親推薦的傳教書籍《荒漠甘泉》。他最常引用的是《荒漠甘泉》以及他父親的著作和言論。

主掌白色恐怖的國家之首 推動民主化進程純屬壓力?
《荒漠甘泉》是一本傾向感性的、抒情式的基督教書籍,不具備宗教改革之後清教徒的嚴謹教義和觀念秩序,對蔣氏父子的治國方略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蔣經國連蔣介石那樣虛有其表的基督徒都算不上,他的行事為人更像史達林那種無神論的獨裁者——在私人感情上,蔣經國的漠然顯得幾近冷酷。為他生下兩個孩子的章若亞被特務殺害,執行這項任務的是蔣經國留俄的同學、特務黃中美。蔣經國的反應呢?「蔣經國先生對這位戴墨鏡的人顯然很不滿意。」蔣經國對手下謀害一個無辜的女人、而且是鍾愛的情人的反應,居然只是「很不滿意」——因為手下乃是奉他父親的命名行事。章亞若死後,蔣經國生前從未單獨接見過姓章的兩個親生兒子。
蔣經國認為,一個治理國家的領導人必須兩條腿走路——計畫經濟與秘密警察。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後者才能抓穩政權。他曾寫信告訴蔣介石,史達林為了提防內部反對勢力圖謀不軌,無情地槍決了八大紅軍將領。打勝仗需要千軍萬馬,但如果敵人在領導人身邊埋藏一兩個姦細,就可以打敗千軍萬馬——這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第二年,蔣介石任命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和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後改為「國家安全局」)。前者是軍隊中的政治機構,後者是「特種監察網組織計畫」的變體。直到一九八八年去世,蔣經國都是台灣情報、安全、特務系統的總掌。他是「白色恐怖」的主要實施者,與史達林的大清洗有異曲同工之處。除了以逮捕、監禁的方法鎮壓反對者之外,他與幾個重大的政治案件很難脫離關係,如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及江南刺殺案。他強調「幹部決定一切」,重視培養幹部、培養青年,也是史達林的工作方法。他在台灣推動「十大建設」,明顯是史達林熱衷於大型工程的特點,與自由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蔣經國從來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在去世前解除了實行三十八年五十六天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和「報禁」,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這可能是他唯一不是在蘇聯學到的東西,這是他在美國和民間的雙重壓力之下,被迫採取的決定。
[1] 為了標明這是其生命中另一個新階段,康生最後一次改名,丟棄了「趙容」之名,採用「康生」之名——意思是「健康的生命」。「生」在儒家傳統中還有學者的含義,康生精通書法,嗜好古書,被譽為中共黨內最具古典文化修養的高官。他的古典文化學養絲毫沒有軟化秘密警察頭子的嗜血本性。
[2] 危險一度逼近蕭軍本人,「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過去曾替王實味辯護過,招待所的人們就說這『有人』是我了」,更有「黑丁在坦白大會上曾指我為日本特務,並說敢於我對證」。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218x150.jpg)
-218x150.jpg)
-218x1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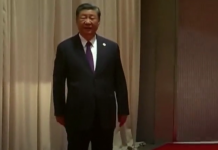
-218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