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是台灣人很強烈的期待,執政黨因應民眾的要求,將於這一次臨時會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只是執政黨提出的是參審制,所持的理由是台灣現行體制較適合參審制,可是多數民間團體期待推動陪審制,雙方沒有交集。不過兩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外國的體制硬塞到台灣,各個都是「外國通」,拿外國的藥方來治療台灣的疾病。
台灣各方面的平均水準並不差,可是多數台灣人的習性卻言必提外國體制,只是外國體制未必適用於台灣,模仿外國體制來改革台灣,往往會挫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育改革,當年教改成員多數屬留美學者,他們將台灣原來的教育制度貶得一文不值,認定美國的制度相當好,因而將美國制度搬來台灣,結果是慘不忍睹,最嚴重的是升學制度。
教改成員認為台灣的聯考制度極端荒謬,一試定終身,違反教育原則,因而將美國的多元化升學制度引進台灣。不過他們犯了一個毛病,認為別人很笨,自己很聰明,所以不會思考台灣為何會產生聯考制度?別忘了中國國民黨佔領台灣初期,並沒有聯考制度,台灣各級學校都各自招生,權貴子女卻走後門入學,例如只要家長拿出十萬元(依目前幣值在千萬元以上),其子女就可進入某私校醫學系就讀。教育行政單位為了消除弊端,入學考試因而演化成聯考制度。
教改成員排斥聯考,因而引進美國多元化入學制度,又將台灣推進弊端叢生的升學制度。教改人士根本就不懂台灣在升學方面的習性與美國完全不同,在美國是學生之間的競爭,台灣則是家長之間的競爭,當年就是要降低家長的影響力才產生聯考制度。目前引進美國多元化升學制度,升學競爭又變成家長的戰場。
以前在聯考制度下,台灣很多傑出人才乃出自弱勢家庭,因為家長的影響力有限。依目前的升學制度,弱勢家庭的子女要出人頭地相當難,因為多元化入學制度又恢復成家長的戰場。教改成員是否知道,目前強勢家庭一個子女的教育經費就超過弱勢家庭全家的生活費,包括子女的教育經費,弱勢家庭的子女要如何與強勢家庭競爭?
目前推動司法改革人士與當年的教改人士一樣,都推崇外國的制度有多高明,而且堅持己見,就是沒有人研討台灣的特質。台灣司法被詬病的就是「恐龍法官」問題,大家爭相推崇外國制度,不考慮是否能解決台灣的問題。要解決台灣司法問題,就該先討論到底是當了法官變成「恐龍」,或是「恐龍」當了法官,顯然的,當然是「恐龍」當了法官,依此邏輯,台灣人具有「恐龍」性格,才出現「恐龍型」的職業法官,既然如此,當然也會出現「恐龍型」的非職業法官,所以無論是陪審制或是參審制,若沒有適當調整,以抑制「恐龍」性格,還是很難挽救台灣的司法。
之所以出現「恐龍」法官,是台灣的人性所造成,敬業精神不佳及對意識的堅持,因而產生偏差的行為,而這些問題並非法官獨有。台灣從事社會或政治運動人士的特色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卻聽不下別人的論述,所以對議題的討論很難有交集。很多熱心推展司法改革人士,對該採參審制或陪審制相當堅持,自己卻沒有完全理解參審制或陪審制的內容,他們本身就是一群「恐龍」,卻要消除「恐龍」,可能嗎?
(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mhchen0201
2020/7/16(台灣時報專論)



-218x150.jpg)
-218x150.jpg)
-218x1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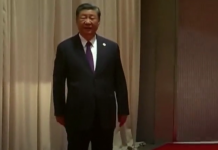
-218x150.jpg)